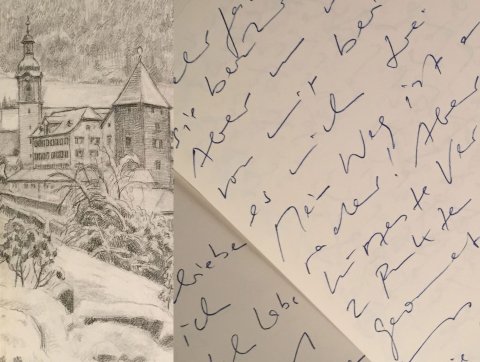
乌尔士是医学博士,主攻脑科学并且在动物脑细胞培养方面造诣很深,有一些独特的技巧。大凡我们所有里有人在脑细胞培养方面遇到什么困难,总是会找他帮忙。刚进研究所的时候,我也跟着他学脑细胞培养技术,如何作小鼠大脑解剖、如何切取大脑内的海马体、如何分离神经细胞、如何配置培养液等等,他都手把手地教我;我跟着他学到了很多手艺……
时间久了,我们也慢慢地成为了好朋友。无论在学术上、教课事宜上或者有关个人的私事,我们都愿意听取对方的见解和评论。每天下班前,我们都不忘到对方的办公室去告个别,然后才各自回家……
乌尔士也是一位十分讲信用、也很在乎宗教礼仪的天主教徒。每年圣诞节前夕,他都会背着满满的背包奔走在各个实验室和办公室……
那天,我正坐在办公桌前整理一些实验的结果,乌尔士扛着一个沉沉的背包走了进来,然后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用精美的礼物包装纸包好的小礼物交给我:“眼看圣诞节就要来临了,与往年一样,我为研究所里的各位同事都准备了一件小礼物。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美文网:www.yafu.me)
我有些不好意思:“谢谢你的好意!可我——没有准备什么礼物……”
他高兴地笑了起来:“这没关系!对我来说,能为大家准备礼物是我的乐趣。所里的同事都知道,你们不必回送礼物……”
我还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可是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来而不往非礼也……”
他又笑了起来:“其实这也算不了什么礼物!我觉得圣诞节不仅仅是一个世俗的欢聚的节日,更主要的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日子,让我们回想过去,展望未来,所以我总喜欢在书店里寻找一些有哲理或者有意义的书送给大家。让大家在圣诞节的空闲时间去静下心去阅读,仔细地去思考一下生活的意义……”
那一年,乌尔士送给我的是一本短篇小说《生命是短暂的》:小说的作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古董商店里发现了一封信,这是一位叫福洛丽亚的女子给一位叫奥古斯提奴斯的男子写的一封情书。很多迹象表明,那个男子就是著名的红衣大主教奥古斯提奴斯。作者用阅读情书作为主线,描写了这对男女之间的恋爱的开始、发展过程以及那突然的结束。最后,写信的那位名叫福洛丽亚的女子在信中用尖锐的语言责问这个男人统治一切的宗教社会:为什么两个年轻男女之间的爱情在宗教的意义上会成为一种罪过?为什么男女间的爱情会被教堂曲解为一个女人对热爱上帝的男子的勾引?为什么奥古斯提奴斯为了忠于上帝而选择放弃自己已经怀孕的爱人?为什么总要让女人成为这个社会的牺牲品?……
乌尔士每年都给同事们送一件小礼物,而那些礼物总是耐人寻味、引人深思……美文
因为病情以及药物治疗的需要,乌尔士从来不沾烟酒,所以和他一起聊天总是「他喝咖啡,我喝茶」。有一次我对他开玩笑地说:“由此可见,我们俩绝不是酒肉朋友,而是真正的「君子之交淡如茶水」”;听了我对其意的解释以后,他急忙纠正我:“对不起,你只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判断。可是,以我所见,我们是真正的「君子之交浓如咖啡」!”
我们在一生中会有很多亲友同事,不管他们得了什么病,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甚至心肌梗塞,我们都会主动去问候他们的健康状况,打听一下自己能不能帮上什么忙。虽然我从进研究所的第一天起就知道乌尔士得了精神分裂症,可是我不敢到他那里去主动问候或者打听,不仅仅因为这牵涉到他的隐私,更因为我不知道该问什么或者怎么去问?因此,我们认识了很多年,我从来不主动向他打听有关他的健康状况或者治疗情况的消息,而是被动地等着他自愿来找我交谈……
有一次,我们俩单独坐在一起聊天,他喝着咖啡,我喝着茶……
他突然直接问我:“我们俩都是学医的。如果撇开教科书里的那些知识,你知不知道得了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一下被他问呆了,不知如何回答,只能歉意地向他摇了摇头……
他告诉我:“以前我跟你提起过,我爸爸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不过他颇有艺术天才,是一位稍有名气的画家,他的很多作品经常在我们州以及各地很多艺术馆里展出。很可惜的是,我得到了他的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却没有得到他艺术天才的遗传。虽然如此,我从小就习惯了去观看爸爸画画,去欣赏爸爸的作品。从那个时间起我就发现,爸爸在病情稳定时期和在发病时期对周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此画的画也完全不一样……”
他坚定地说:“这种经历,再加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我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其它人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坐标系统……”
听后我有些迷惑:“生活在不同的坐标系统?——对不起,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他好像早就预料到我的回答,继续向我解释:“因为你我都生活在各自的坐标系统,所以我很难向你直接解释自己的感受——因此,我只能设法举一个例子来形象地向你解释……”
他微微地想了一会儿,然后向我解释:“在一个夏天的晌午,到处阳光灿烂,大多数人都在外面游敖嬉戏,欣赏那些洁白如玉的荷花、巍峨高耸的山峦以及湖上绮丽清秀的波涟;有一小部分人在一个电影院里,电影刚结束,里面一片漆黑,他们都焦急地等在电影院的门前。那扇电影院的大门突然被打开,灿烂的阳光顿时普照遍地;在这一瞬间,这一小部分人看到的四周却充满了闪耀的星点,灿烂的色彩和飞翔的幻影……”
他好像故意地停顿了一会儿,让我有时间去感受这一瞬间:“此时此刻,那些「大多数人」和这些「一小部分人」虽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拥有同一个环境,而且在同一个太阳的照耀下,可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却决然不同——那么这里谁对谁错呢?其实这里原本没有「真相」和「错觉」可言,所有人看到的都是「现实」,只不过他们各自看到的都只是自己所在的坐标系统里的「现实」……”
说到这里,乌尔士的脸色变得有些严肃:“你也知道,我在19岁左右第一次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发作。也就是说,在这之前的19年的时间里,我一直生活在「大多数人」的那个坐标系统里,学会了用「大多数人」的目光和标准来判断这个世界。「精神分裂症发作」意味着,我被迫去生活在「一小部分人」的坐标系统里……”
我入神地听着他的叙述,半点都不敢出声……
“以后,不管我一时的感受如何,我总是终生难忘那「大多数人」的坐标,更重要的是,我所做的一切,都会被大家用「大多数人」的目光和标准来审判。也就是说,在实际生活中,「大多数人」的坐标系统永远是主导的,是唯一正常的;而其它的都只是病态的坐标偏差,只是病态的「错觉」而已……”
说到这里,他又停了一会儿,然后急忙解释说:“请你不要误解!我丝毫不想批判「大多数人」的坐标系统,更不想美化精神分裂症!我只是想借此机会表明,对患者来说,精神分裂症是他一辈子的伴随者。因此,患者必须在这一辈子里同时接受两个坐标系统,必须同时生活在其中,而他们这一辈子所作的一切却只能用一种主导的坐标系统来衡量,所以他们很难成功——所以他们都活得很累……”
他又补充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的药物治疗确实能帮助我们这些精神分裂症患者去成功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那时,我虽然医科大学毕业了好多年,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这么形象化地、直接地、一针见血地向我作过如此的解释!此时此刻,我无言答对,更不知自己该如何直接面对……
不管怎么说,这次对话彻底地改变了我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视角……内容来源:雅赋网(www.yafu.me)原文网址:https://www.yafu.me/a/201601/85097_2.html
相关专题:




 很好奇,后来呢?
很好奇,后来呢? 
